爱廉说 | 张维屏(清):洁身自好诗抒怀
千年羊城,文脉绵延;
先贤清风,浸润心田。
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广州市纪委监委在“廉润羊城”系列融媒体宣传中,创新推出《爱廉说》音频专栏,为您讲述广州古今清廉人物故事,让我们一起感悟廉洁之志,涵养清风正气。
“官虽廉,虎饱食;官而贪,虎生翼。”这是清代中后期著名爱国诗人张维屏的一句名言。张维屏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以及咸丰四朝,先后在湖北、江西任州县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他为官清廉,被誉为“尽心民事,深洽舆情”,后终因不耐官场的腐败,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辞官归里。本期《爱廉说》为大家讲述清代廉臣——张维屏的清廉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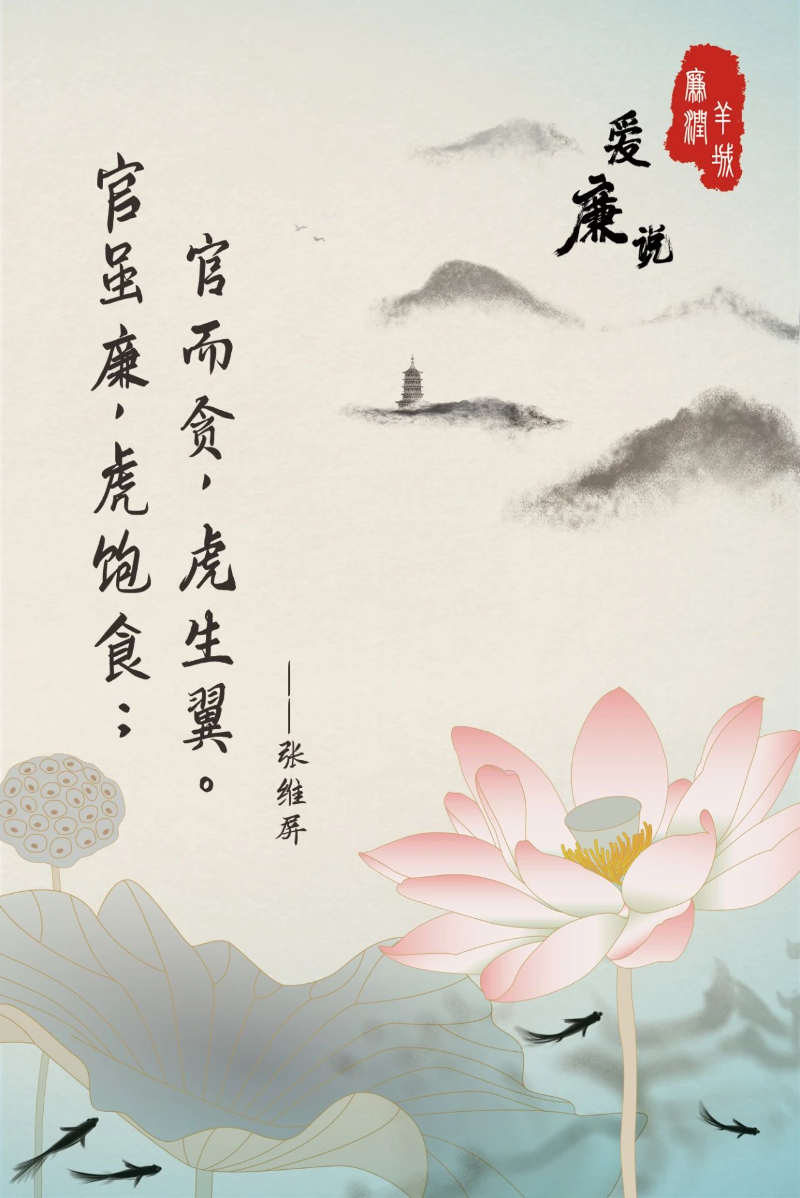
张维屏(1780-1859年),字子树,号南山,又号松心子,晚号珠海老渔,清代广东番禺人;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与黄培芳、谭敬昭二人并称“粤东三子”。
张维屏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东广州)。父张炳文是清嘉庆年间举人,曾出任四会县县学训导,长于诗文。张炳文后受聘于当时广州十三行著名的行商潘振承家族,担任馆师。张维屏随父入潘氏馆学,与潘氏子孙一同研习经史,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
张维屏十三岁时,参加县试,位列榜首,名震乡里。嘉庆九年(1804年),应考乡试,中举人。本应可赴京赶考会试,但张维屏为人仁孝,见祖母年弱体衰,不忍赴京故留乡侍奉。在此期间,他肆力诗文,诗才愈加精进,诗名远播。
嘉庆十二年(1807年),张维屏第一次赴京赶考。期间与在京文人切磋赋诗,当时已年逾古稀的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文学家翁方纲在阅读了张维屏的诗作后,不禁发出“诗坛大敌至矣”的感叹。张维屏未及而立之年,就受到翁方纲这样的文坛名宿的高度赞赏,使得他的诗名鹊起,广为人知。
可惜的是,他虽在文坛初露锋芒,但却未能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及第。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而言,“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植在他们心里,无论自己在文坛上取得多么骄人的成就,金榜题名依然是他们终身追求的梦想。张维屏亦不例外,他并未因为一次的失败,就轻言放弃,而是坚持不懈地开始了他在科举路上的“漫漫征途”。
张维屏的“科举梦”直至道光二年(1822年)才得以实现。当年,他顺利通过会试,在由道光皇帝主持的殿试中,考取了二甲进士。同年四月,出任湖北黄梅县县令,由此正式踏入仕途,开始了“十载以来,四为县令”的官宦生涯。在相对短暂的仕途生涯中,他几乎均在地方任职最高官至四品知府,虽没有位极人臣,但在地方任上,却能始终坚持以百姓福祉为依归,勤政爱民,被时人称赞为“尽心民事,深洽舆情”。他敢于揭露官场的黑暗腐败,对深受贪官盘剥的百姓抱以深切的同情。
年逾不惑,经数年努力,张维屏终于金榜题名。在一偿夙愿的同时,张维屏立志做一名施政为民的父母官。他曾写下著名的诗篇《新雷》,表达自己欲兴利除弊,万象更新的壮志。
张维屏:造物无言却有情,每於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赴任黄梅县的第二年夏天,黄梅县遭遇水患灾害,张维屏亲赴救灾一线视察灾情,为受灾百姓发放救灾物资,与百姓同甘共苦。张维屏用诗歌形象地记录下了黄梅官民众志一心,齐抗水患的壮观场面。
张维屏:三面环江水,江高逼岸低。千人培尺土,万户仗孤堤。伐木新桩急,鸣钲众力齐。心劳身转健,中夜立涂泥。
在另一首叙事性的长诗《黄梅大水行》中,有一小注写道:“余出抚恤,舟为急水冲去,力抱大树,乃免于难。”当地民众唱和道“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在小农社会中,百姓抵抗天灾的能力很弱,一遇旱涝常常有心无力,难以招架。张维屏心存百姓,事必躬亲,得到了黄梅百姓的嘉许。其后张维屏调任长阳县令,百姓都前往相送。
张维屏未到任长阳县,又受命调任广济县知县。广济县乃长江重要的漕运枢纽,每年漕运收入颇丰。广济知县,官位虽低,但却是人人艳羡的“肥差事”,历任知县在任上“发家致富”者不在少数。张维屏则不为所动,且不愿意将过重的漕运征粮任务加诸在百姓身上。他认为,漕运如不大量征粮则难以保证粮食的供应;但如果过多地向百姓征粮,百姓定会不堪重负。面对这一矛盾,他无力调解,更不想将漕运压力施加于黎民百姓身上,故选择了引疾求去。许多人对他引疾求去的行为表示不解,或笑其沽名钓誉,或笑其不识时务。仅有少数人理解其矛盾的心情。蒋攸铦曾言:“数年以来,(张维屏)以名进士出为县令,所至咸得民心。夫救人所难,而南山处之井然。收漕,人所乐,而南山辞而决然,即此可知其为人矣。”汪廷珍也认为,张维屏引疾求去是“欲求心之所安”,不想自己成为鱼肉百姓的“帮凶”。
后来,张维屏先后出任襄阳府同知,江西泰和县知县,吉安府通判以及南康府知府等职。期间,因其文采人品出众,多次被任命为地方乡试考官。道光七年(1827年),其父亲张文炳逝世,遂返乡丁忧三年。丁忧期间,受聘为广州学海堂学长,潜心著述,培育英才,为家乡文教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丁忧服阕后,他前往江西任职,针对当地蝗虫泛滥成灾的现象,张维屏总结前人治蝗的经验,撰写一篇名为《治蝗述略》的短文。
十年的宦海沉浸,让张维屏渐渐意识到,康乾盛世以后,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以及固有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土地兼并情况愈演愈烈,官民之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自己一人的清廉自守,难以拯救百姓苍生,故由此感到失落和愤懑。当然,他并未选择同流合污,而是在继续保持洁身自好的同时,更多地用笔尖揭露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
张维屏回顾自己宦海十年,将诸多感慨写成近似于歌谣的组诗,名为《县言》,对清朝中后期地方官场的诸多“怪相”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评。如《蝇头篇》对科场内抄袭之风有过生动的描写。
这首近乎童谣的诗歌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乡试科场作弊的手法以及考生与官员沆瀣一气的现象,感叹科举识人选才之难。
张维屏“十载以来,四为县令”,辗转湖北、江西各地,对地方官场肆意欺压百姓的现象以及地方官场的衙门习气颇有体会。他在《衙虎谣》中写道:
张维屏:衙差何似猛虎,乡民鱼肉供樽俎。周官已设胥与徒,至今此辈安能无?大县千人小县百,驾驭难言威与德。莫矜察察以为明,鬼域纵横不可测!吁嗟乎!官虽廉,虎饱食;官而贪,虎生翼。
在这首歌谣当中,张维屏将地方胥吏僚属形象地比作猛虎,在地方肆意鱼肉百姓。清代任官,执行严格的回避制度,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任官,如任官地与原籍相距较近的亦须回避;乾隆初年以后,无论原籍、寄籍(离开原籍后长期居住的地方)均需回避。且地方官员流动亦较为频繁,张维屏自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使得地方官员在施政时不得不依靠乃至依赖一般生长于本土的胥吏或僚属。这就为地方胥吏势力不断壮大提供了可能,某些胥吏家族甚至延绵数代,关系盘根错节,往往难以驾驭。地方官虽为胥吏之上司,但由于“人生地不熟”,流动性亦较大,即使有心整治,亦有心无力。张维屏任官十载深知胥吏之横行霸道,有些官员更连同胥吏一起盘剥百姓,百姓敢怒不敢言。
又如,《狱卒威》中所言:“狱卒威,狱囚苦。初入狱中如地府,不肯出钱加苦楚。”张维屏的笔墨着力描写了监狱中环境的黑暗以及狱卒人心的黑暗。回忆起自己为官时视察监狱后的情形以及后续的措施,但仍是不禁对狱囚悲惨的遭遇表示无限的同情。
张维屏虽看到了诸多官场乱象,但却无力回天,遂萌生了“一官无补苍生,不如归去”的念头。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毅然告病辞官,返乡过起了闭门著述,授徒讲学的生活。在广州,他又一次被任命为学海堂学长,其后前往广东东莞宝安书院讲学。但这种半耕半读的闲适生活并未持续多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军在珠江江面上向清朝军队发起攻击,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闲居在家、胸怀一腔爱国热情,并且与当时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文人士大夫林则徐、魏源素来交好的张维屏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年逾花甲的张维屏看到英军对广州的疯狂进攻,怀着一腔热血写下了《书愤》。
1841年5月,少数英军在广州三元里奸淫掳掠,激起三元里人民的抗英运动。三元里人民与邻乡民众一起拿起手中的锄头镰刀,与英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三元里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英勇事迹深深感染了这位寓居在家的六旬老人。在了解整件事情的始末后,张维屏以诗歌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三元里民众抗击英军的过程,歌颂了人民力量的可贵。
咸丰九年(1859年),年届八旬的张维屏目睹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曾经繁华的广州城,在战火的洗礼下,也变得萧条。他不禁写下了“八十老人谈异事,广州城里少行人”的诗句。在这一年,张维屏走完了他八十年的人生历程。带着对国家和民族无限忧思离开了人世。他一生创作的诗歌不下两千首,题材丰富多样,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音频内容改编自《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
《爱廉说》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委指导,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制作的一档反腐倡廉音频融媒体栏目。



